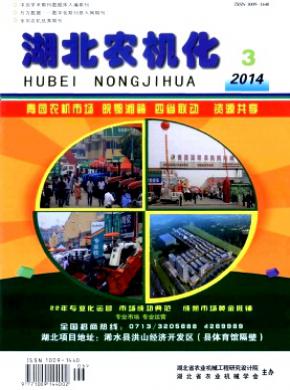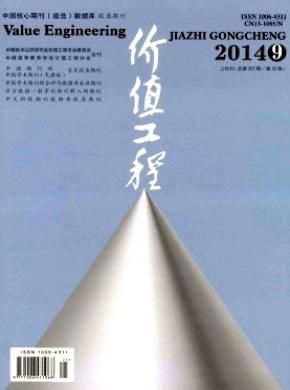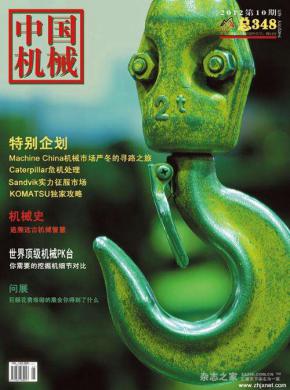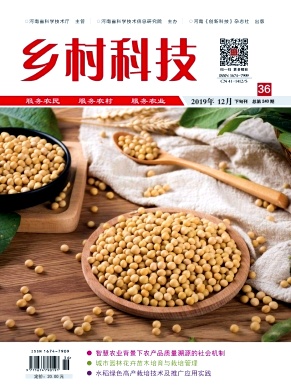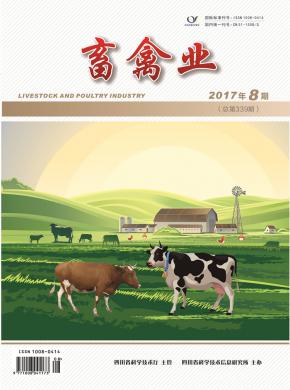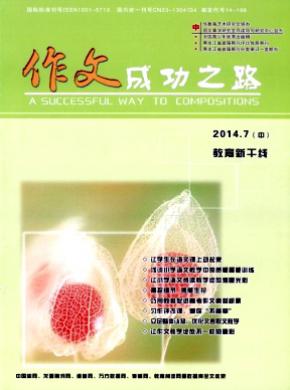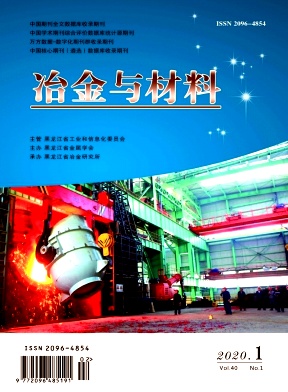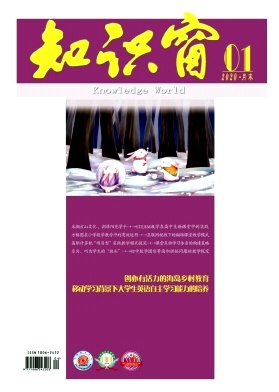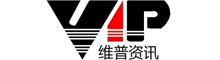神經科學家說,我們的大腦實際上無法“重新連接”自己
幾十年來,在研究中反復顯示,在中風、截肢或突然失去視力或聽力后,大腦具有非凡的自我連接能力。至少,我們都是這么想的。
現在,寫在電子生活兩位神經科學家——塔瑪·馬金(Tamar Makin)和約翰·克拉考爾(John Krakauer)——認為,該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實驗并不能最終證明大腦可以在功能上重組自己。
“我們的大腦具有驚人的自我重組和重組能力,這個想法很有吸引力。它給了我們希望和迷戀,尤其是當我們聽到非凡的故事時。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克拉考爾。
“這個想法超越了簡單的適應或可塑性——它意味著對大腦區域的大規模重新利用。但是,盡管這些故事很可能是真的,但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解釋實際上是錯誤的。
在他們看來,沒有一項關鍵研究符合認知重組的最嚴格定義,即通常致力于一種計算的大腦部分能夠進行完全不同類型的認知,其特征是功能或行為的變化。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審查的規范研究都沒有令人信服地滿足這些標準,”他們寫.
Makin是劍橋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教授,她的研究重點不同能力的成年人(例如假肢患者)的神經可塑性極限。
Makin 和 Krakauer 一起——誰有興趣在中風康復中——親眼所見在“先天性失明、耳聾、截肢和中風等神經系統侮辱”之后可以做出的“令人驚訝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行為變化”。
一個明顯的認知重新布線的突出例子來自2000年發表的新生雪貂研究.
在這個實驗中,來自雪貂眼睛的神經輸入通過手術連接大腦的聽覺皮層而不是視覺皮層。盡管有這種混淆,雪貂還是有一些遠見后續研究.聽覺神經元已經重組了自己,以執行新的功能。
“但這是真正的重組嗎......?”問馬金和克拉考爾。在視覺皮層中完成的處理類型可能就像聽覺皮層所做的處理一樣,這意味著這種手術重新布線并沒有真正挑戰大腦改變其功能。
如果將相同的輸入傳遞到大腦中負責完全不同過程的部分,例如前額葉皮層,結果可能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
當研究參與者奇跡般地恢復了被認為因受傷或損傷而喪失的認知功能時,大腦很可能通過依靠以前存在但非常安靜或未充分利用的神經連接或功能來增加計算能力,作者認為.
例如,當即使在連接該特定胡須的神經被切斷后,老鼠仍然能夠移動胡須,作者很可能總是將相鄰胡須上的神經調到受損的胡須上認為.無需重新布線!
同樣地當剛出生的小貓的一只眼睛暫時縫合時,這加強了活躍的眼睛,削弱了不可用的眼睛,導致第二只眼睛睜開后會出現一些“非常笨拙的小貓”。
然而,這并不能證明大腦重組。神經元很可能一開始就對來自兩只眼睛的輸入很敏感,當一只眼睛不可用時,“增益”就會增加.
作者說,如果看起來大腦的一部分正在做一些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那可能只是一種錯覺,因為我們一開始就不知道大腦有這種額外的能力提出.
研究人員還懷疑大腦是否“接管”了未被使用的神經元,并“重新連接”它們以執行其他功能。
例如,患有先天性白內障的兒童(先天失明)可以在手術后立即恢復視力。
“如果視覺皮層被重新挪用以支持新功能,那么視覺輸入的恢復將是徒勞的(或者至少需要實質性的重組逆轉),”作者寫.
“但事實并非如此。孩子們不僅能夠立即感知到一些視覺信息,而且表現出對視覺錯覺的敏感性。
雖然大腦的相互聯系和“模糊”比我們想象的要多,但Makin和Krakauer認為,大腦的不同部分注定要執行某些功能,即使在早期發育中,也不可能偏離這種潛在的“架構”或“藍圖”。
“很多時候,大腦的重新連接能力被描述為'奇跡'——但我們是科學家,我們不相信魔法,”說馬金。
“我們看到的這些驚人行為植根于努力工作、重復和訓練,而不是大腦資源的神奇重新分配。
本文發表于電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