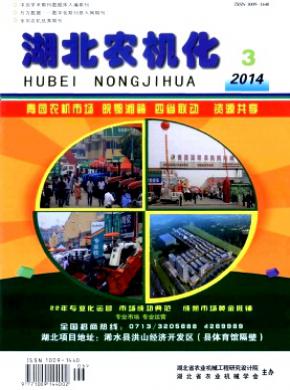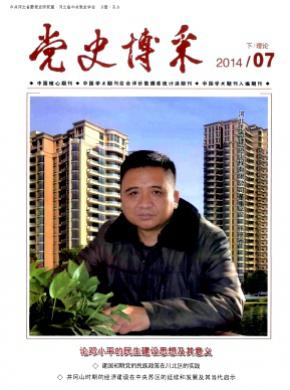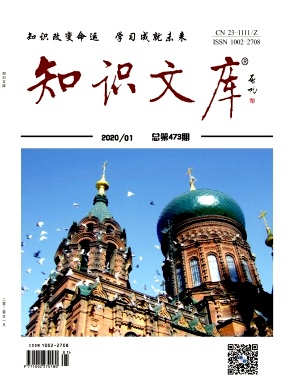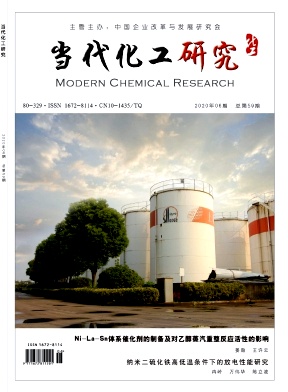您如何撰寫同行評審的期刊文章?
首先,你不會寫一篇同行評議的期刊文章。你寫一篇文章并發送出去進行同行評審,這將反過來決定它是否被發表作為同行評審期刊中的同行評審期刊文章。
其次,同行評審依賴于對知識的理解擴大——不限于已知和確定的內容。因此,不能簡單地根據與現有知識、方法等的一致性來確定物品的價值。
像這樣想。人們在玩游戲。有裁判。在一場普通的比賽中,規則已經存在,裁判可能從來沒有真正參加過比賽,他們可以被設置為規則是否被遵守或違反的權威,并最終決定“誰贏了。”但是這個游戲有點不同。玩游戲就是弄清楚游戲是什么以及它的規則是什么的過程。并不是說它很混亂:事實上,如果你在不知道發生了什么的情況下作為旁觀者看待它,它可能看起來與普通游戲沒有太大不同。但規則永遠是他們自己在玩.因此,唯一能理解規則的人是玩家——因為規則是由玩家創造的。所以裁判必須自己是球員——不能有“外部”權威……觀眾也不能把自己放在裁判的位置上……只有球員才能真正“得到”正在發生的事情。只有他們在游戲中占有一席之地。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游戲……通常,這些游戲安家變成更普通的。球員成為老師,充當學生的裁判,他們現在是在玩“游戲”而不是真正的“游戲”。這些游戲規則更加清晰,是為思考和研究的“真正游戲”做準備。
對同行評審的需求以及同行評審的問題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在“真正的游戲”——這個不穩定的游戲中——同齡人作為裁判員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將真實游戲同化為游戲游戲的常態,甚至冒著顛倒它們之間必須存在的關系的風險。真正的比賽同行裁判開始將自己視為裁判作為權威 他們強加自己的異質的規則就像他們一樣這規則,即使在與同齡人打交道時也表現得像老師一樣。但它也通過用同齡人代替裁判來打開游戲,它總是進入常態,真相的波動性。
或者換句話說:同行評審——同行裁判——體現了一個矛盾。它既是成為對等的權威,又是成為權威的對等。
所以,回到問題:有不撰寫“同行評審期刊文章”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是成為某個研究人員社區的一部分并玩他們的游戲。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艱難的過程。在某些方面,這是痛苦的,因為它涉及將思想和想象力的力量提交給社會控制,而這往往是自決和內在的最后保留。那些學術個性受取悅欲望或赤裸裸的野心驅使的人發現它最容易。那些最深的人,發現它是最困難的。它需要奇特的心靈智慧——極端的劃分。
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比喻是,正式舞蹈的研究之于身體之于心靈。正如編舞是世界上最接近無規則游戲的事物,其觀眾不能成為裁判。(當然,歌劇、舞蹈、古典音樂的裁判觀眾很多——但這始終是一種防御機制。經驗,不亞于體育迷對分數,統計數據的癡迷……)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既殘酷又解放的紀律。換句話說,同行評審是一種精神鏡子——正如舞者的鏡子并不完全是為觀眾而立,而是為了旁觀本身。正如舞者總是被迫面對他們的意志和他們的身體之間的不匹配——身體對意志的抵抗,試圖將其推向極限并達到某個步驟、姿勢、手勢——研究人員被迫面對論證意圖與其實現之間的不匹配。
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學者,作為研究人員,即使不是懶惰,也往往既受虐又自我放縱。他們一生都在努力爭取只有通過服從才能獲得的解放。他們崇拜某種個人自由,為之奉獻自己的生命,但相信他們必須通過不斷的自我強加活動使自己配得上這種自由,以免他們被內疚所淹沒。真理會讓你自由,但前提是你成為它的工具。但是,當然,由于真相呈現出有形的形式——因為“真相社會”體現在它的法官身上——受虐狂很快就會變成虐待狂。匿名同行評審服務于社會學功能,允許放縱、發泄,虐待沖動是學術界產生的受虐傾向幾乎不可避免的對應物。這幾乎就像天主教懺悔。如果你有罪惡的想法,懺悔會讓你享受它們,甚至不用付諸行動……
當然,對于正派的人來說,擁有可以被濫用的權力的想法就足夠了……僅僅與一個人分享一個罪惡的想法就足夠了……同情,溫和,清醒,愛最終勝出。但是,唉,情況并非總是如此......